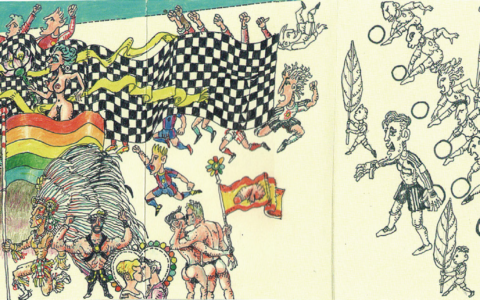本期刊物的主題定為「新藝術對文遺舊建築的活化」,可能是一種反思,正在漸進實驗中的本澳文化政策的一個方向,如何能以更好的方式被具體實踐。
一座一成不變的老建築,它可供傳播的文化內涵有限,通過觀光價值而產生的新的社會效應也有限。為了不對建築內部造成過多的使用耗損,在文化象徵的體面意義上損害文遺品格,文遺不可輕易挪作實用用途。這時,新的藝術創作和老建築的結合,對這座旅遊城市而言,幾乎成了最好的選擇之一。
體現時代的公共性審美

通常情況下,一座歷史文物建築,會是一件值得紀念的藝術,它會比一件繪畫或雕塑,其設計和實施得更審慎,並且也更少設計師(建築藝術家)私人的風格色彩,更多體現時代的公共性審美。其空間佈局,不僅跟實用有關,還與那個時代的世界觀、精神氣質的投射有關,就像潘諾夫斯基,將哥特式建築的結構視為經院辯證法思維一樣。
基於使用目的,老建築被劃分設計建造的空間,本身也是一種象徵空間:那個時代、那個地域人的生活方式,既反映在建築空間的合理安排上;而具體的建築規劃習慣,反過來約束了那時那地人的生活方式。
新的藝術行為進入這樣一個空間,就是在與過往的時代/世界對話:不得不對話,否則就變成一個牽強的、與建築互害的、掉價的藝術活動。對話,則既能激活對舊建築本身審美特徵的再認識、再理解,又能給進入到空間中的藝術家,在對話的過程中激活新的可能。
劇場藝術相通之處
本期刊物的主題,似乎首先根源於劇場藝術對歷史建築的二次適應,對於美術範疇領域的當代藝術,則與劇場藝術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與話劇不同,很多時候,美術展的空間本來就是文遺建築。一些壁畫、浮雕、聖灶畫,本來就是配合建築所製的美術品。

因此,如果我們要談論現在這個主題,無疑是談論更具挑戰性的相互介入和適應:例如,一件當代藝術作品,擺進一所原功能為教堂的建築裡,則何如呢?當然這個例子比較誇張,因為教堂的數量過餘,需要二次利用,這種奢侈的奇特現象,大概只可能出現在西方。
對於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參考國外:在國外,有各種不同的舊空間被激活作藝術空間,在特定空間中的藝術項目,會由駐留藝術家根據特定空間去新創,體現出藝術家對這一空間的理解。
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和實際項目空間適應相性很差?那就想方設法,在協調中,迸發新的張力啊!以合適的形式體現的既對立又能臨時協調同置,不是給當代藝術創作最大的加分項嗎?在不對建築的基本構件,產生不可還原的損害的基礎上,二次設計是完全可行的。但改造肯定不能是往白立方去貼近:與其刻意弱化原有用途的空間特性,做到半吊子的空間一般化,不如針對性地,保留、甚至還原出原建築用途的細節特性,再讓新的藝術活動和舊特性對話。

舊監獄改造成藝術駐地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國外甚至有將舊監獄改造成藝術駐地項目空間的先例。伊利亞·卡巴科夫的《從自己的房間飛向太空的人》,來自前蘇聯集體公寓建築的結構。真實的單元間房屋結構,當然也可以在一個白立方展廳裡臨時搭建,但在通過燈光昏暗的走廊,走進各個原先就在那裡的小房間時,這件空間裝置作品可以更好地呈現。每個房間內,都擺放了讓觀眾對房間主人職業、生活狀態、人生理想等事情展開聯想的場景和物件。
藝術家可以此濃縮地佈下一個時代的群像全景故事——通過一個或獨立、或刻意加強代表性的小個體。也可以天馬行空,給枯悶的現實生活注入自由的想象:這裡有個人,從這個房間,用自制的低科技裝置,成功地飛進太空了!

發佈者:雷徠,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3/01/28/%e6%b4%bb%e7%94%a8%e6%96%87%e9%81%ba%e5%bb%ba%e7%af%89%e7%a9%ba%e9%96%93-%e7%95%b6%e4%bb%a3%e8%97%9d%e8%a1%93%e7%9a%84%e7%a9%ba%e9%96%93%e4%bb%8b%e5%85%a5%e8%88%87%e9%81%a9%e6%8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