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健文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視覺暨媒體人類學博士生、國際文化評論人,努力嘗試用中、葡、英、法、德文寫作,至今發表文章以葡文、法文居多。實驗民族誌短片《小說無用》導演。
文:張健文、蜜嘟(Mathilde Denison)
圖:蜜嘟、Lucía Inthesky、Michael Zagar
「我們本來就生於知識之中。像我這樣出身於地方資產階級的人,不就正正是吃知識的奶長大的嗎?甚至是上小學之前,我們就已經浸淫在一種環境、體制內,做人、上進的準則就是要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做班上成續不比人差的學童。從小我們就在競爭,一直在知識中沐浴、嬉水。這算是『走運』嗎?我寧願儘量跟這一切都斷絕關係,但既然我無法做到,我就以找到新路向、更多的支路,甚至是玩把戲為己任……努力去找仍不屬於、但應該成為知識的事物。」
以上內容引自法國思想家傅歌(陸譯福柯,台譯傅柯、傳科等)1975年接受法國重量級主持澤桑舍(國音尚謝爾)採訪時的電台錄音,澤桑舍問到傅歌是如何能「走進知識當中」,又問傅歌這是否算是「走運」。
戰後法國文壇、藝壇、影壇、樂壇可謂星光熠熠,風雲人物輩出。澤桑舍的經典專訪至今仍為法文世界聽眾津津樂道。另一邊廂,傅歌一生的批判思想對當代和後世的影響均甚為巨大,其多部鉅著亦以難懂見稱,不過面對著澤桑舍和廣大法國聽眾,傅歌除了是幽默的,更是易懂的、全沒架子的文人,訪問中甚至為澤桑舍的一些最簡單直接的問題而「困住了」。

說到歷史,漢字「史」甲骨文中象形手有所持,同「吏」、「事」、「使」均視為同源,這樣跟法字「歷史」(histoire,粵音熱事拖哇)語源有可相比較的地方。法文此字源於拉丁文,拉丁文中又出於古希臘文「ἱστορία」,本義是系統探索後的成果,其詞根則是「ῐ́στωρ」,即識法律者、智者。毋可置疑,史學家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和話語權,像哲學一樣,要追溯到古希臘文明。不過,古希臘的「史書」或者不能同今天的歷史研究相提並論,阿拉伯文中也有直接從古希臘「ἱστορία」得來的借詞,意思卻是冠冕堂皇的神話、故事、傳說。
筆者從《知識考古學》、《考掘》理解到傅歌的意思是:「史書」讓我們習慣並且了解到「歷史學者」的工作正正是在研究過程中使其發現的歷史痕跡「說話」。歷史上,這些「痕跡」(又譯「印跡」)曾被視為凝固在時空中的客體(法文又有「物件」等意思)長埋於黃土中,等待「歷史學者」(此書漢譯「歷史學家」、「史家」)的發掘。這個主體(哲學用語,指「歷史學者」)將通過讓客體成為「事實」,也就是說要在這些「痕跡」上強加一種「意義」、一種「知識」。對「歷史學者」工作的這種描述似乎完全跟「考古學者」的方法吻合。細讀《知識考古學》、《知識的考掘》的這些譯名時要非常謹慎,因為如果傅歌用到「考古學」這個詞,他其實要指的卻是另一回事。正如這位「哲學家」接受澤桑舍專訪時道出:「『考古學』一詞係惡棍用字」。
儘管傅歌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鮮明的史書色彩,但在《知識考古學》、《考掘》中,他還是再次避免以(當年透過法文可閱讀到的)「歷史學者」姿態寫作。在這部鉅作中,作者將之分為五個部分(〈引言〉或〈緒論〉、〈話語的規律性〉或〈話語的規則〉、〈陳述和/與檔案〉或〈「聲明」和檔案〉、〈考古學的描述〉或〈「考掘學式」的描述〉和〈結束語〉或〈結論〉),傅歌採用了個人特色甚濃的「考古學」方法論,不過更應說傅歌其實是借「考古」之名,對當時傳統且保守的史學進行批判。
他既注意到不將歷史「痕跡」視為不動之客體,也小心不把「歷史學者」看作為「痕跡」加上意義的主體。另外要注意的是,雖然中文有在幾種譯本中加上〈引言/緒論〉、〈結束語/結論〉,但其實原文目錄中似乎是故意避開這樣的「前言後語」區分。
在《知識考古學》、《考掘》中,歷史知識不再基於史書過去、甚至是今天也能見到的那種主、客關係。這位思想家質問作為其特指的「陳述」(「聲明」)或「話語」的歷史知識,與這些「陳述」(「聲明」)或「話語」(歷史知識)所講述的歷史「痕跡」或「事實」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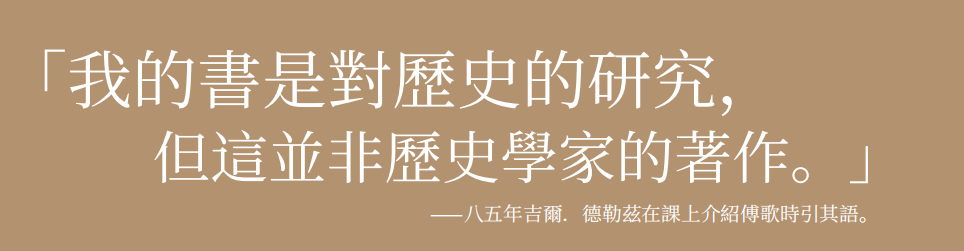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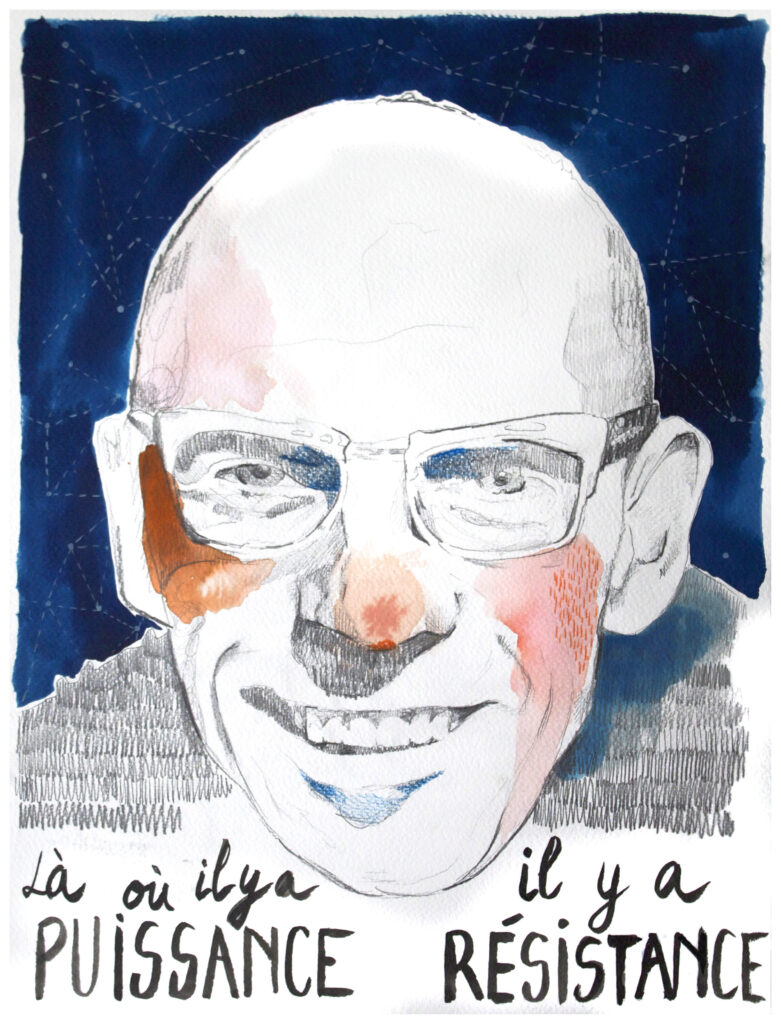
「陳述」(「聲明」)和「話語」法文分別是「énoncé」和「discours」,內含傅歌複雜的理論,不少華文資料也有介紹,在此不贅述。前者「énoncé」(粵音欸弄些)是過去分詞的名詞體,看拉丁文分拆此字是見有前綴「e-」(出)和源自「nuntius」(傳話人)的詞根,本義就是「道出」、「說出」。後者「discours」(粵音跌事孤,又有「演講」等義),可作拉丁文詞源分解為前綴「dis-」(離),詞根則是「跑」,也就是「跑離」,後來也引伸出表達「傳話」的意思。
此外,傅歌文本中的「陳述」(「聲明」)在儒家世界分別有「言表」(慎改康之日譯)、「言表」(李正雨韓譯)和「發表」(維基百科越譯)等譯,而「話語」則譯為「言說」(日)、「言舌」(韓)、「演言」(越)。歐洲語文中、羅曼諸語外舉例德譯「Aussage」、波譯「wypowiedź」跟法文完全對等,詞源均為「出⸺說」(說出),但跟法文不同的地方是這些都更似是日常用字。這樣「望文生義」的作用是為了了解到亞歐幾種語言的繙譯同原文的微妙關係,儒家世界引用西方哲學用語時常常需要重新譯製一些概念或把新義加到舊詞中,但西方世界常常其實都是「就手」,直接使用到其語言中的用詞,所以用洋文讀起來,文本好似是明(所以要非常小心),用中文讀時則要再三翻看。
《知識考古學》、《考掘》所分析的正是歷史「知識」的形成。正如他之前的作品一樣,傅歌並不滿足於僅為一個時代的心態或行為作歷史記錄,而這部作品亦更接近於哲學家而不是「歷史學者」的著作。傅歌一直表明,其方法就是「發掘」出不同時代各種心態和行為的環境。
在傅歌的學術生涯中,他對監獄、學校、醫院等機關和系統的批判,又或是他對權力理論和精神病學的評論在不同的文本中變得越來越複雜。他的著作似乎難以看懂,但他的目標其實旨在讓當時過於守舊的學術思想得以向時代推進,也就是要打破知識至高無上的權威。生於巴黎以外「地方」資產階級的傅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吃知識母乳」長大的,然而他從來都不認為他是「走運」。恰恰相反,傅歌正是從這種資產階級知識的觀念中,終其一生都在試圖擺脫自己的過去。
聆聽傅歌多個專訪錄音可以看出,他總是以一種簡單、生動、合適又貼近聽眾的方式說話,毫無疑問:傅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真切的左翼分子,盡畢生之力,讓更多人「走進知識當中」,聽到當時知識國度中被視為不堪登上大雅之堂的聲音。作為一個言行一致的大學者,傅歌一生都通過他的著作和政治參與關注弱勢群體,譴責不同權力機制在知識生產和傳播中的操控,致使那些從未能成為「知識」的事物,最終也能列入史冊。
(拙文原文係同比利時藝術工作者、漢學人蜜嘟合作以法文寫成,葡文版在本澳《城與書》中刊出,並加上了對「知識」詞源的評論。現在的中文版本並非法文原文的繙譯,而是希望更貼近中文閱讀習慣而重寫的,必要的引文翻譯亦是盡量不採用直譯。法、中版本都是筆者二人協力下筆的。另外,拙文的其中兩張附圖由西班牙藝術工作者Lucía Inthesky和俄羅斯設計師Michael Zagar無償借出刊登,筆者均表謝意。)
發佈者:張 健文,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s://fantasiamacau.com/2022/06/23/%e5%90%8c%e5%82%85%e6%ad%8c%e4%b8%80%e8%b5%b7%e4%bd%9c%e7%9f%a5%e8%ad%98%e7%9a%84%e8%80%83%e6%93%9a/






